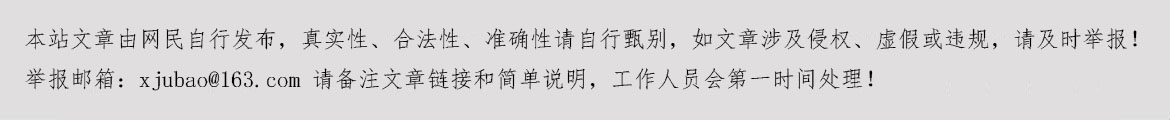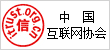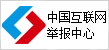“为什么不爱我了?为什么鄙视我?”
2021-10-15 09:33:11
差旅费报销 https://www.cloudpense.com/
影评人、记者里卡尔多与妻子埃米丽亚结婚的前两年,两人挤在租来的小房子里,生活窘迫,但婚姻还算和美;后来,为了赚钱买下那间妻子喜欢的公寓,里卡尔多与制片人巴蒂斯塔合作,担任影片《奥德赛》的编剧,从此“把灵魂卖给了魔鬼”。
在里卡尔多看来,自己与妻子的关系恶化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她不再如以往般需要陪伴,还表现出种种抗拒。原本他只将爱的消退归为妻子对自己新工作的不满,直到在一次争吵时听见她脱口而出的“我鄙视你”,开始陷入更多怀疑、猜测和想象。
里卡尔多一直试图搞清楚自己被“鄙视”的原因,同时并没有停止带埃米丽亚与他和巴蒂斯塔一起工作。本文摘编自意大利小说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的《鄙视》,在这三段文字中,他先想起两人“不匹配”的出身,然后发现疑似对方“出轨”的证据,最终自己也不知道该将这“鄙视”置于何地。
01
“我如今不仅不被人爱,
而且还受到鄙视”
[晚宴前,里卡尔多和埃米丽亚在家里吵了一架,埃米丽亚怒称“鄙视”他。]
正如我所说过的,埃米丽亚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只上过小学,读过几年师范;后来,她辍了学,去学打字和速记,十六岁就开始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雇员。她原出生于一个人们所说的殷实人家,她家过去在罗马郊区有一些田产,生活富裕。但因祖父搞投机生意破了产,家产挥霍殆尽,父亲生前一直在财政部当小职员。因此,埃米丽亚是在贫困中长大的,所以在文化教养和思考方式上几乎就是个平民女子;跟某些平民女子一样,似乎处处都标榜着自己所谓的见多识广,以至于有时执拗得近乎愚蠢,至少是思想狭隘。但她有时还真能以令人完全意想不到而又莫名其妙的方式,发表相当尖锐的看法和评价;就像普通百姓往往比有些人更接近于自然本性一样,任何世俗观念和偏见都无法泯灭她的良知。她发表的某些见解都是经过她深思熟虑的,所以她的言谈往往是实在的、中肯的、坦率的。可是谁若是不理解她的这种坦诚,她就会不高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坦诚和中肯恰恰验证了她所发表的见解本身的真实性。
所以,那天当她冲着我喊“我鄙视你”的时候,我立时深信她说出的这句话的真实含义,这句话要是从别的女人嘴里说出来也许不说明什么,而由她的嘴里说出来就意味着:她真的鄙视我,而且现在已无法挽回了。即使根本不了解她的脾性,单凭她说话所用的语气,就使我深信无疑:那是发自内心的纯真话语,是以往从未说出口的,是她迫不得已不假思索就脱口而出的话语。就像有时候,从一个满口土话、说话颠三倒四的农民嘴里偶尔冒出一句充满哲理的警句,一针见血而又合乎情理,它要是出自他人之口不足为奇,但出自一个农民之口,似乎就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了。我痛苦地注意到她在说“我鄙视你”这几个字时的语气,与她头一次向我表示爱的时候说“我爱你”时的语气一样,是那么绝对真切。
我对那几个字的坦诚和真实性没有任何怀疑,我双手颤抖,两眼无神,手足无措地开始在我的书房里来回踱步,脑袋里什么也不想,这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埃米丽亚说出的这几个字像是几根针扎在我的感觉器官里,越扎越深,越来越令人疼痛难忍;我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痛苦,除了这种痛苦,别的什么也感觉不到了。最令我痛苦的自然是意识到我如今不仅不被人爱,而且还受到鄙视;不过,由于根本无法为这种鄙视寻找到任何理由,哪怕是最小的理由,所以我深感委屈,同时也感到害怕,我生怕实际上我并没有什么可委屈的,生怕她鄙视我在客观上是有根据的,只是我没有意识到而已,但对别人来说却是显而易见的。我自尊心强,但那是令人同情的自尊:就像一个命运不济的不幸的男子,他是绝对不该受到歧视的,相反,更应受到尊重。埃米丽亚的那句话动摇了我的自尊心,它使我第一次怀疑自己是否认识自己,是否不善于评估自己,是否完全脱离现实而始终沉溺于自我陶醉之中。
我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情绪颓丧,无精打采。我对那天以及随后的日子里可能发生的一切,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不管会发生什么。埃米丽亚还在她的卧室里睡觉;我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磨蹭了好久,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我慢慢地回到了因为睡眠而暂时忘了的令人厌恶的现实。我回顾着所发生的一切,心想,我得决定究竟接受还是不接受《奥德赛》这部影片剧本的编写;我得弄清楚埃米丽亚为什么鄙视我;我得设法重新赢得埃米丽亚。
我说了,我感到精疲力竭,心力交瘁,无能为力了;用这种近乎打官腔的方式综述目前我生活上所面临的这三个要害问题,无非是异想天开地想拥有我远远达不到的精力和才智,这一点我很快就发现了。一位将军、一位政治家、一位商人会用这种精力和才智把要解决的问题尽快地解决掉,他们会胸有成竹地做到对问题了如指掌,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问题处理好。可我不是这种人,而是与他们恰恰相反。我觉得,当时我自欺欺人地以为我拥有的那种精力和才智,一旦要采取行动,去解决问题时,就会完全荡然无存了。
不过,我意识到自己有这个弱点;尽管我是闭着眼睛仰躺在沙发上,我发现自己一旦想出能摆脱这种现状的办法时,就又停止遐想,重又抱着希望飘飘然起来。这么一想,就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我似乎看到自己已当起《奥德赛》的电影编剧来了。我似乎从埃米丽亚那里也得到了解释,并且发现那表面看来是那么可怕的鄙视,实际上只是幼稚的误会;最后我跟埃米丽亚又重归于好了。不过,我这么想象着时,发现自己只不过是在为自己勾画着梦寐以求的、圆满的大结局而已:这样的结局与现实状况之间,不仅存在着一片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填补的空白,而且用什么去填补都无济于事了,哪怕是些十分坚实和十分有黏性的东西。总而言之,我希望能按我最良好的意愿去解决问题,但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去解决。
我迷迷糊糊的,不知什么时候重又睡着了。
02
“过去我无缘无故地受到鄙视,
而今我有充分的理由来鄙视他人了”
[晚宴中,里卡尔多看到巴蒂斯塔吻了埃米丽亚的肩,认定两人“私通”。]
我跟埃米丽亚不是在结合几十年之后,而是结合几个月之后就出现了危机,根本谈不上什么同生共死,尽管我们期盼“面容憔悴,白发苍苍”仍相爱如初。我曾经向往过我们的关系能像预想的那样,这令人费解的关系破裂使我好梦难圆,为此我感到惊愕和恐惧。为什么?我真想到把埃米丽亚关在其中某个房间的别墅里去寻求答案。我转过身去,背对着大海,朝窗子站着。
我站在阳台的一角;这样,我可以不被人发现地斜着看到客厅里面的一切。我抬眼一望,看到巴蒂斯塔和埃米丽亚两人都在客厅。埃米丽亚穿着我们第一次遇上巴蒂斯塔时穿的那件黑色的低胸晚礼服,站在一个活动的小酒柜旁;巴蒂斯塔正俯身在酒柜上,用一个大水晶杯子调制鸡尾酒。埃米丽亚脸上那种既茫然又从容、既尴尬又充满欲望的不自然的神态,使我猛然一惊:她站在那儿,等着巴蒂斯塔递给她酒杯,同时还茫然地环顾四周,看得出她原来那种惆怅迟疑的神态已荡然无存了。巴蒂斯塔调完了酒,小心翼翼地把两只杯子斟满,并直起身子把一只酒杯递给了埃米丽亚;她像是从心不在焉的状态中惊醒过来,慢慢地伸手去接杯子。那时刻,我的目光全部倾注在站在巴蒂斯塔跟前的埃米丽亚身上了,她身体微向后仰,一只手举起酒杯,另一只手搭在一张扶手椅上;我情不自禁地注意到她把裹在光灿灿的紧身衣下面的胸部与腰部推向前方,像是想献出自己整个身体似的。不过,她的脸上没有任何献媚的表情,相反,却保持着往常那种犹豫不决的神情。最后,像是为了打破那令人尴尬的沉默,她说了几句话,并把脑袋转向客厅尽头壁炉旁边的一排扶手椅;为了不让满杯的酒溢出来,她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于是,我预料到的一切终于发生了:站在客厅中间的巴蒂斯塔赶上了她,用一只手臂搂住她的腰,把脸贴近她那高出他肩头的脸。她立刻拒绝了他,但并不带严厉,而是用一种活泼或是开玩笑似的恳求的目光示意仍捏在手指间高举着的酒杯。满脸堆着笑的巴蒂斯塔摇晃着脑袋,搂得更紧了,他的动作是那么猛,以至于正像埃米丽亚所担心的那样把她的那杯酒都洒了。我想:“现在他要亲她的嘴了。”但我不了解巴蒂斯塔的性格和他的粗鲁。事实上,他没有亲她的嘴,而是把她肩上的衣领捏在手里使劲地往下拽,都扯破了。此时,埃米丽亚赤裸着一个肩,巴蒂斯塔低下脑袋,用嘴紧贴着她的肩;她直挺挺地站在那儿,像是耐心地等着男人吻完。但我注意到在巴蒂斯塔吻她的肩时,她的面容和目光仍然像往常一样迟疑和茫然。随后,她朝落地门窗这边望了望,我似乎觉得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看到她做了一个恼怒的手势,用一只手拿扯下来的肩带捂住胸口,急匆匆地从客厅走了出去。这时,我也离开落地窗,朝阳台另一边走去。
埃米丽亚已经不爱我了,用她的话来说她鄙视我,实际上她是已跟巴蒂斯塔相好而背叛了我。这样一来,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原来我还觉得莫名其妙,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过去我无缘无故地受到鄙视,而今我有充分的理由来鄙视他人了;埃米丽亚的一切神秘的举动现在都可以用“私通”这种极其简单的词来加以解释了。也许,一开始从爱情的角度出发的这种最庸俗而又最合乎逻辑的考虑,让我当时对发现埃米丽亚的不忠(或者说是我觉得的一种不忠)并不感到有什么痛苦。然而,当我迟疑而又木然地走近阳台的栏杆时,却突然又感到了痛苦,而且,我反常地认为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不可能是事实。我自言自语着。埃米丽亚只不过是让巴蒂斯塔吻她;但并不是因为这个,也不是因为现在我有权利鄙视她了,我心里的委屈就因此而神秘地消失了,这一点我明白;甚至,不知为什么,尽管亲眼见到了巴蒂斯塔吻了她,我觉得她似乎仍保留着鄙视我的权利。实际上是我错了:她并不是不忠于我;或者说,她的不忠只是表面的,还需透过表面现象去挖掘她这种不忠的深刻根由。
我记得,她对巴蒂斯塔一直有一种我难以解释的根深蒂固的反感情绪;就在当天早晨,一路上她曾两次恳求我别让她跟制片商单独在一起。我怎么能把她的这种态度与那个吻联系起来呢?毫无疑问,那是第一个吻:很有可能,巴蒂斯塔是抓住了那天晚上难得的一个好时机。那么说,我还没有失去什么,我还可以弄清楚为什么埃米丽亚顺从巴蒂斯塔;因为我隐隐约约地感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那个吻而有所改变,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她却仍像以往一样,甚至比以往更有权利拒绝我的爱,并且鄙视我。
人们一定会说,那不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时候,我唯一应该做出的反应首先就是冲进客厅,让两个情人知道我目睹了一切,但是我很长时间以来就在琢磨埃米丽亚对我的态度,显然我是绝不可能猝然做出这样冒昧而又天真的举动来的;再说,我并不太在乎找出埃米丽亚的差错,我更在乎的是弄清楚我们的关系,闯入客厅里就完全排除了弄清真相和重新赢得埃米丽亚的可能性。我告诫自己说,得三思而行,处在那种既微妙又难以捉摸的境况下,必须小心慎重才是。
我之所以在客厅门口停住脚步,还出于另一种考虑,也许这是更为自私的考虑:当时我有充分的理由使编写《奥德赛》电影剧本的计划落空,让我最终能摆脱那个我所厌烦的工作,而重新去干我所喜爱的戏剧创作。这种考虑,对于我们三个人,埃米丽亚、巴蒂斯塔和我,都将更为有益。实际上,那个吻标志着我与埃米丽亚之间模棱两可关系的结束,我与我的工作之间模棱两可的关系也同样就此结束。我总算解开了这个疑团。但我必须从容不迫地逐步采取行动,而不能弄得满城风雨。
03
“不管我是不是被人鄙视,
我都深信自己并不是可鄙的人”
[晚宴后,埃米丽亚向里卡尔多“挑明”,认为他故意把自己推给巴蒂斯塔。]
事情是挑明了,或者至少是以我们俩可以接受的那种方式挑明了,但那都是我过去就已经知道了的。糟糕的是:我本以为埃米丽亚鄙视我的原因也许可以通过审视我们过去的关系去寻求;可是,她却不想承认它,实际上,她是想继续毫无道理地鄙视我,并排除我为自己辩护和解释的可能,因而也就排除了她自己重新尊重和爱我的可能。
总而言之,我明白了埃米丽亚那种鄙视我的感情,早在我能用自己的行为做出真正的或意向性的辩解之前就产生了。鄙视产生于我们俩长期以来性格的碰撞,这已无须再通过什么重要的、令人信服的试验,就像人们无须用试金石去碰击贵重的金属从而检验其纯度的做法一样。事实上也是如此,当我大胆提出她不爱我的原因是产生于她误解了我对巴蒂斯塔的态度时,她既不认可,也不否定,只是缄默不语。我突然痛苦地想道,实际上,埃米丽亚从一开始就以为我是一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人,而并没有责备我是用主观猜测来断定她的感情。换句话说,在埃米丽亚对我的态度上,有一种对价值的衡量,一种对我性格的看法,这跟我的行动是毫不相干的。而我的行动似乎又证实了她的那种衡量和看法;不过,即使没有证实,她也完全不可能以另外的方式来衡量我。
其实,如果需要的话,证据就在她那怪异神秘的举动之中。本来她一开始就可以通过跟我真诚坦率地交心而消除残酷地窒息了我们之间爱的那些误会。但她没有那么做,因为正像刚才我说过的那样,实际上她是不想消除误会,而愿意继续鄙视我。
我一直仰卧在躺椅上。我的这些思绪令我情不自禁地感到烦躁不安,我木然地站起身来,走过去俯身靠在栏杆上,双手搭在上面。我凝望着那么宁静的夜色,也许,是想让自己平静下来。当海上刮来的一阵微风吹拂在我那滚烫的脸上时,我突然想到自己不该感到这样轻松,我意识到,只要这种鄙视还持续着,被鄙视的人是不能也不该去寻求平静的。就像受到最后审判的罪人,虽然他可以说:“高山啊,把我覆盖起来吧;大海啊,把我淹没了吧。”然而,即使他躲到最隐蔽的地方,鄙视都一直跟随着他,因为鄙视已渗入他的心灵,无论他到何处都将带着这种受人鄙视的心情。
于是,我又那样躺在了躺椅上,用颤抖着的手点燃了一支烟。不过,不管我是不是被人鄙视,我都深信自己并不是可鄙的人,我有聪明才智和文化素养,这一点甚至连埃米丽亚都承认,这乃是我的骄傲和应该受到别人尊重的资本。我必须得思索,无论我思索的对象是什么;不管我面对什么神秘莫测的事情,我都应该大胆地运用我的聪明才智。如果我放弃运用聪明才智,那我真的要为我假设的可鄙而感到沮丧了,尽管那是未曾证实过的假设。
于是,我重又固执而清醒地思索起来。我的可鄙究竟表现在哪儿呢?赖因戈尔德无意中对我说过的话语此时又萦绕在我的脑际,他把我和埃米丽亚之间的关系,跟奥德修斯和珀涅罗珀的关系相提并论:“奥德修斯是个开化的男人,而珀涅罗珀是个未开化的女人。”总之,赖因戈尔德用他对《奥德赛》的荒诞解释,无意中点破了我和埃米丽亚之间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就像阿喀琉斯所射之矛,先伤害人,然后又治愈人。现在,那解释本身却给予我某种安慰,我被他说成是“开化的人”,而不是“可鄙的人”。我发现如果我愿意接受的话,这种宽慰相当灵验。实质上,我是个处于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境遇之中的文明人,拒绝使用暴力的文明人,在对待至高无上的名誉问题时能通情达理的文明人。然而,一旦我把事情捅破,类似这样的解释——权且说它是一种传统的解释吧——就不再令我满意了。且不说我和埃米丽亚的关系是不是真的跟奥德修斯和珀涅罗珀的关系那么相似,这我很没有把握,另外,这种在历史范畴内无疑是有效的解释,在完全超越时空、超越良知和纯属个人内心情感的领域里,就不那么有效了。在此,支配一切的是我们内心的感受。历史只能在它本身的范畴内说服我和开导我,而我当时所处的境遇,不管它有多少“历史的”原因,使我确实都不想在那样的处境中工作和生活。
可是,埃米丽亚为什么不再爱我,为什么鄙视我呢?尤其是她为什么需要鄙视我呢?突然,我想起了埃米丽亚说过的那句话:“因为你不是个男人。”她那句女人家的陈词滥调却是以坦诚的口吻说出来的,这令我十分震惊;而且,我想,埃米丽亚对我的态度的关键也许就在那句话中。那句以否定的语式说出的话里,隐含着埃米丽亚心目中理想的男人形象,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得像个男人:照她看来,那正是我所不具备的,而且,也是我做不到的。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那句话是如此平常,如此粗俗,使人觉得埃米丽亚心目中理想的男人形象并不是产生于对人的价值的有意识的体验,而是从她所生活的世界的那种世俗眼光出发的。现今世界上,一个称得上是个男人的男人,就要像巴蒂斯塔那样有兽性的力量和平庸的成就。头天在饭桌上她望着巴蒂斯塔时所流露出来的那种近乎赞赏的目光就已向我表明了这一点,而且也证实了她由于绝望而终于屈从于他的欲望这个事实。总之,埃米丽亚鄙视我,她愿意鄙视我,尽管她真挚而又单纯,或者说,正因为她的真挚和单纯,她才完全落入了巴蒂斯塔布下的罗网。在那罗网中,贫穷的男人是无力挣脱富裕男人的摆布的,或者,换句话说,是无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的。埃米丽亚是不是真的怀疑我出于利益关系而想成全巴蒂斯塔的美意,这我没多大把握。然而,要是真是这样,她也许会这样想:“里卡尔多得靠着巴蒂斯塔,他是受巴蒂斯塔聘用的,他很想从巴蒂斯塔那里再得到其他的工作,巴蒂斯塔追求我,所以,里尔卡多就暗示我做巴蒂斯塔的情妇。”
本文节选自
《鄙视》
作者: [意]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译者:沈萼梅、刘锡荣
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 读客文化
出版年: 2021-7
编辑 | 巴巴罗萨
主编 | 魏冰心